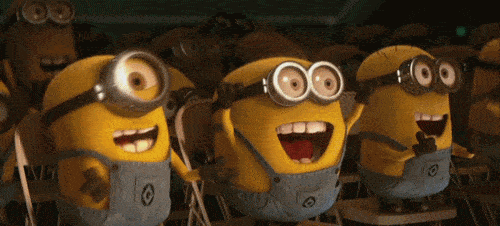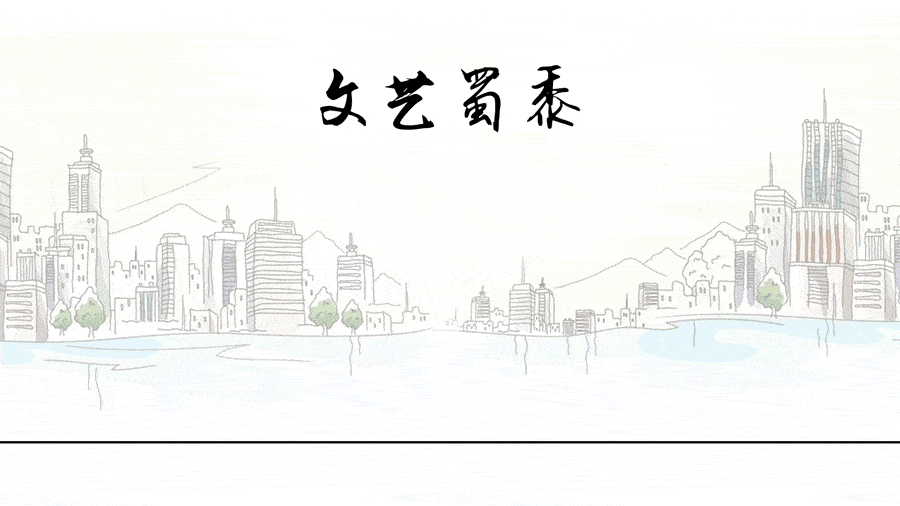戴名世戴名世(1653~1713),字田有,一字褐夫,号药身,别号忧庵,晚号栲栳,晚年号称南山先生。死后,讳其姓名而称之为“宋潜虚先生”。又称夏庵先生。江南桐城(今安徽桐城县)人。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己丑科赵熊诏榜进士第二人。
戴名世始祖于明洪武初年由婺源迁入桐城,至戴名世已历十二世。戴名世的曾祖父戴震(字孟庵)是明末诸生,当明清易代之际,怀着-之痛,削发为僧,隐居龙眠山中埋头著书。祖父戴宁(字古山)明末曾任江西新淦、乐安县令,政声卓著,推为良吏,后以养亲解官归田,数十年中以酒度日,隐逸而终。父亲戴硕(字霜崖)为人忠厚,因故国沦亡,生活艰辛,内心忧苦百端,无一日忘怀朱明
王朝,48岁那年病逝于陈家洲教馆。临终前告诫戴名世说:“吾其死于忧乎!吾死,祸必及子,然勿效我忧也。”戴名世是戴硕长子,父丧既孤,本自殷实的家境,也在明末张献忠农民起义军围困桐城时“一败而不复起”。
戴名世自幼聪慧过人,1周岁开口说话,到5岁已能吟诗作对,6岁启蒙读书,11岁就能熟背《四书五经》。15岁时,他作的八股文就被人们纷纷传抄,当作范本。家境衰落后,戴名世凭才干教授门徒而自赡,倒也安逸。后来,他觉得制义这种文字不足以传世,就悉心研究古文和史学,他决心要在文学上,继承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而在史学上继承司马迁。
戴名世家中贫寒,无力购置大量的文史书籍。要想读到这些书,他只好走亲访友,到处借阅。戴名世如饥似渴地大量阅览书籍,借来的书往往难以满足他的需要。有位朋友笑着对他说:“要满足你的书欲,恐怕只有南乡潘木崖先生家里的藏书了。”潘木崖是个饱读诗书的明朝遗老,清朝灭明后,他矢志不作官。但是,众所周知他家中有数以万计的藏书。不过,他家的藏书从不外借;即便在他家阅读,也要看你是否真有才学、是否可造就。当时,潘木崖对戴名世的名气也略有所闻。但是当戴名世登门造府请求借阅时,他还是要亲自试试他的才学。于是,他笑着对戴名世说:“借米可充饥,借钱可医贫,先生要借书何用?”戴名世一听,知道这是在出对联要他对,略加思索,他便恭敬地应道:“学经以明道,学史以晓义,小子惟学问是求。”对的十分工整。潘木崖心中暗喜,点点头又问:“看来戴先生名不虚传,但不知你要先看什么书?在这里看几天?”戴名世回答道:“我白天给学生授课,只能夜晚前来,今夜就让我读秦汉史吧!”潘木崖惊讶地问道:“你一夜能读完几十部的秦汉史?”戴名世点点头。潘木崖准备下书籍和蜡烛,然后离去;戴名世自个儿钻进书堆中去了。第二天一早,潘木崖起床,见戴名世也从书房出来了。潘木崖迎头就问:“说实话,你昨夜到底读了几本?”戴名世答道:“全读完了。”几十部书的秦汉史一夜读完,潘木崖有点怀疑,就从书中挑出几十个典故考考他。戴名世对答如流,毫无差错。潘木崖这才信服了,又问他:“你看书的速度怎么这样快?”戴名世笑着回答:“一目十行呀!”潘木崖不禁翘起拇指,赞扬他说:“目及十行称才子!”戴名世紧接着回敬下联:“家藏万卷谢恩师。”潘木崖哈哈大笑。从此,两人以师徒相称。这就是“一目观十行”的故事。
戴名世十七八岁时,喜好交友且同游,常邀县内名士聚会饮酒,砥砺名节,研讨文章。康熙十九年,戴名世补县学生员,成了秀才。这一年,他28岁,相继授课在本县陈家洲,邻县舒城。康熙二十三年秋,出应乡试落第。次年,以文行兼优得贡生。至此,两次赴南京应乡试均落第。康熙二十五年冬,戴名世在督学使李振
玉的鼎力推荐下,进了国子监。在京师,早已名冠江南的戴名世立刻引起人们的关注。尚书韩菼折节与交,为他的怀才不遇而叹息不已。大学士张英
“以乡戚故”,几次聘他为家庭教师,教授他儿子张廷璐等学业。后来,戴名世还在旗人官学任教。他以精于八股制义出名,时文稿一脱手,出版商争着付梓刻印。他之所以编选供学生模仿的八股文,是为了学习、研读科举中式试卷,以充实自己,准备再应考。于是,天下都在诵读他的时文。但是他的同乡方苞却说:“此非戴名世的文章”;戴名世也常说“此非吾之文也”。虽然他早已是一位撰写文章的才子,但是,他在应乡试时一而再,再而三的落榜。康熙四十年(1701)他出版了第一部文集《南山集偶钞》,如此题名是为了寄托怀念故乡南山之情。康熙四十一年,戴名世回归故里。他的弟子尤云鹗、方正玉开始刊刻他的文集《南山集》发行。原版藏于方苞家。后来,经过多年努力,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终于通过了乡试,戴名世中举时,已经53岁了。康熙四十七年,他刊行了一部新版《四书》,题名为《四书大全》,全部沿用宋代儒学家朱熹的注疏。康熙四十八年,戴名世参加会试,中贡第一;再赴殿试,戴名世终于在年逾50时,获得一甲第二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
戴名世的文才之名已露端倪,而“福之祸所倚”,祸也由文字而起。戴名世的学问以史见长,喜欢考稽明代的逸事,时时借文章以自我抒怀,愤世、郁闷、气逸不可控御。康熙五十年(1711)赵申乔因他的儿子与戴名世同科应考时谋私、受戴名世报怨,他处心积虑设法参劾戴名世。赵申乔参劾所凭依据是戴名世早年出版的《南山集偶钞》中的一封信。这封信是康熙二十一年戴名世写给他的门生余湛的。信中他让余湛寻找一个曾在朱由榔宫中执事的和尚,此人曾口述过朱由榔朝廷在云南、贵州时的情况。余湛即将此人口述记录寄送戴名世。其中某些叙述与方孝标所写的《滇黔纪闻》有所不同。吴三桂叛乱时,方孝标正在云南。在这封信中,戴名世明确表示他有志于搜集即将散失的南明朝廷史料,并且拟定撰写一部南明信史。而在信中引用了南明年号,而未用清朝年号。此外,他与他的弟子倪生写了一部书,论述修撰国史的常例。书中讲清朝国史应该从康熙纪元作开国定鼎的起点。理由是顺治虽然已入关,然而历经十八年之久,三藩之乱并未平息;而且承祀明朝的南明尚在。如果按历史上蜀汉之称的先例,那么顺治不能算已成正统开国者。此书却被与戴名世有仇的赵申乔家得知并且告密,指出戴名世撰文诽谤本朝,并且被视为目无清朝,大逆不道。于是文字之狱降临戴名世头上,惨遭杀害,祸及全家。康熙五十二年初,方、戴两家宗族和与戴名世交往过的学者、或曾为戴氏著作写过序言的人,都被刑部列入处死刑名册。清廷兴此大狱,部分原因似乎是由于一种错误的假定:认定方孝标与方光琮有亲属关系。方光琛是安徽翕县人,曾在吴三桂叛乱政权中任过大学士。但是,清圣祖康熙却下谕减缓如此严酷的量刑,结果只有戴名世被处死。方孝标虽已去世多年,仍被开棺戮尸,诸子及全家均充军黑龙江
。其他被株连的人,包括方苞与汪颢均被判往汉军旗人家为奴,但后来都予复籍。此事史称“南山集狱”。而告发戴名世的赵申乔一直被世人所讥讽。
据说,在戴名世临刑这天,皇帝特地派一名翰林去监斩。并且对这位翰林说:“临刑前,你要出个对子让他对,对不出照斩,对得出暂缓刑。”这话被赵申乔暗中打听到了,便私下对这位翰林说:“戴名世才气压人,留下来对你、我都不利,不管他对得出对不出,你都一律照斩。”这位翰林本来就是赵申乔的亲信,自然要秉承他的意见办事了。这天,寒风凛冽,天昏地暗,一代才子戴名世披枷带锁,被刽子手押到了刑场,那位翰林此刻正在思索着那个上联。恰好,有个木匠因造宫殿失误,被逮捕下狱,从他身边经过,他顿时受到启发,念一上联道:“木匠做枷枷木匠。”戴名世毫不迟疑,对答如流:“翰林监斩斩翰林。”戴名世本是翰林,令那位监斩的翰林大吃一惊,他硬是咬牙切齿地下令:“斩!”戴名世就这样被屈斩了,时年61岁,葬于桐城南山冈砚庄。
当时,戴名世的所有著作均遭禁毁。道光二十一年(1841)以后,戴氏族人戴钧衡将戴名世的部分文章及历史著作,辑集刊行。这部文集共十五卷并年谱一卷。此书未敢以“南山集”做题名,而题为《宋潜虚先生集》。并且未敢收招祸的文字,而著者也不敢实署戴潜虚。由于戴姓源流出于宋姓之后,在不得不避讳戴姓时,以宋潜虚署名来代替。因为春秋战国时曾有过姓戴的人过继给宋戴公的后裔,用宋姓即取自此意。
戴名世是与桐城派散文名家方苞齐名的又一大家。他年轻时,常邀集县内才华出众者二十人研讨文章。他以曾祖父《响雪亭铭》中“不阴常雨,盛暑犹雪”题意,撰成《响雪亭记》一篇,道尽故里风光,极言人情时态,被广为传诵。同里著名学者潘江,对戴名世非常赏识,誉其文有司马迁、韩愈之风,热心出借家中藏书供其研读,被戴名世视为终生之师。由于家贫,戴名世20岁即授徒养亲,以精于时文倾动天下,“文稿脱手,贾人随即为之刊布以售”。但他的志向却在古文与史学,戴名世也常说“此非吾之文也”。前辈的熏陶,社会的黑暗,世情的淡薄,铸就了戴名世独特的性格特征:纵情任性,狂傲不羁,却又时时充满幽忧之思,常常悲歌至于泣下,故而落笔为文,慷慨愤激,自快其志,如此狂简,自然为世俗所不容。
戴名世曾经往来与燕赵、齐鲁、河洛、吴越间,到过这些地方,他方才闻听到向来有学问的学士们对他的赞誉和羡慕,连名士韩菼、方苞等也心中折服。戴名世是康熙年间一位颇有影响的文学家。他有不少风雅逸事,一直在民间流传。
据说,有一年的五六月间,戴名世与方苞一起应邀来到沙溪镇讲学,这里文人学子设宴款待他俩。酒过三巡,雅兴大作,于是,他们高谈阔论,谈古论今,吟诗作赋。戴名世、方苞更是才华横溢,技压群芳。突然,有位名士向戴名世、方苞劝酒说道:“桐邑大邦,不少七斗二五升才子。”方苞忙谢道:“过奖了!”戴名世心想这不只是夸奖,也是在出联考我们。便不假思索地答出了下联:“沙溪小镇,也有四斤十六两先生。”席间顿时爆发出一片赞扬声。原来所谓“七斗二五升”是把才高“八斗”有意拆开来讲的。而戴名世的“四斤十六两”也是故意将“五经”(“五斤”的谐音)拆开来对的。确实是出得巧对,对得也绝妙。
戴名世、方苞走出沙溪镇,忽然见到路途上有个老叟把一担梨子横放在中央。等二人走近时,那老叟说出上联:“一担重梨拦子路”。这句话表面上是指一担重梨拦了你们的路。其实“重梨”是“仲尼”,“拦”是“难”的谐音,而“子路”是仲尼的学生。含意是说:“我这个仲尼要难一难你们这些学生。”老叟敢如此抬高自己,显然不是等闲之辈。戴名世有也点犯难,方苞一见此景,便拉着戴名世往回走。还没有迈出两步,戴名世灵感突发,他又把方苞拉回来,朝着老叟笑笑,然后说:“两个夫子笑颜回。”表面上是说我们俩人笑颜满面地回来了。其实暗含着把自己比做仲尼(孔夫子的名字),把老叟比做孔夫子的学生颜回。而“笑”字含有可笑不自量的讥讽之意。原来,那个“老叟”是个不服戴名世的儒生装扮的。到这时,他谦虚地说:“班门弄斧,学生冒犯了!”
戴名世、方苞从沙溪镇来到安庆去游塔。赶到塔前,一群人都争着要先登塔,戴名世、方苞挤不进去。这时,从里面走出一个-,只听他扯着嗓子喊:“我出一个对联,谁能先对出就先上。”只听那-说:“宝塔六七层,直竖钢鞭驱白日”。话音刚落,戴名世就对上:“城墙千万垛,倒生牙齿咬青天。”一阵喝采声过去,戴名世拉着方苞进去登塔。那-忙止住方苞,又说出一个上联:“宝塔六七层,层层设门,门朝东西南北;”方苞一时懵住了,戴名世指着他身上揣着的历书,这一暗示,方苞灵机一动,马上说出:“历书十二页,页页有节,节载春夏秋冬”的下联。在场上又响起的一片喝采声中,两人就游塔去了。
满腹经纶的戴名世,在长期清贫淡泊生涯中,养成胸襟坦荡,豪爽放达的性格。
他轻慢权贵、鄙视豪门,是个不苟钻营,青天白眼,使酒骂座,桀骜不驯的一代狂士。
康熙二十六年(1687),戴名世已经35岁,为家中死丧债务所迫,冒着严寒远走京城,靠教授诸经谋生。
这一年,戴名世在一个翰林家设馆授徒。主人对这位饱学之士,相见恨晚,引为知己,礼节待遇都有所加重。此时,一位与戴名世同时入太学的选贡生,正巧是翰林的远房姻亲,也在翰林家设馆教授。
有一天,翰林轻骑简从,自郊外归来,一进门就直奔戴名世书斋,非常困倦,倒身仰卧在戴名世卧榻上,汗水涔涔,气喘吁吁地说“今日座骑不驯服,又行路太多,令人疲惫不堪。”那位姻亲正好在他身旁,认为天赐良机,立即为翰林又是端盆倒水,又是捧壶送茶,还为他 身体,捶揉双腿。虽然已经汗流浃背,仍然不想歇息。不料此时,翰林对这位姻亲格外殷勤地作为,看在眼里,烦在心上。他大声呼叫正在撰写文章的戴名世,问:“戴先生,世间什么样的人最为可恶?”戴名世轻蔑一笑,答道:“献媚邀宠的人最可恶!”翰林笑着说:“也不尽然,献媚的人因为好媚者所致,所以好媚的人最为可恶。”他的姻亲听了两人一席话,脸色骤变,神情困窘,红着脸辩解:“当今之世,何人不好媚,又何人不媚人呢?”戴名世一听,放下手中笔,哈哈大笑道:“我就从来不逢迎吹捧人!”戴名世声音洪亮,震得窗纸沙沙作响。翰林听了,也从床上起身,说“我就讨厌那种逢迎吹捧的人!”那位姻亲听罢两人的对话,面红耳赤,悄然走了出去,戴名世和翰林望着他离去的背影,相视一笑。
著有《孑遗集》、《南山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