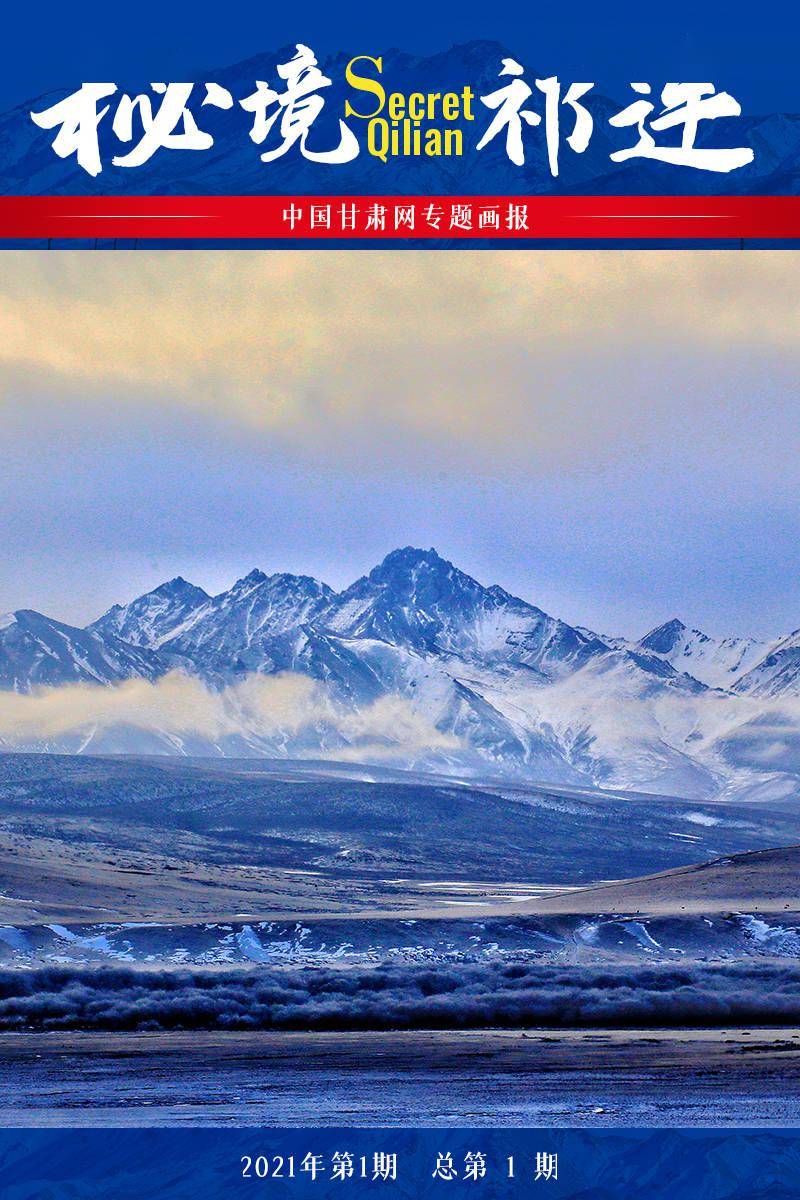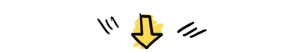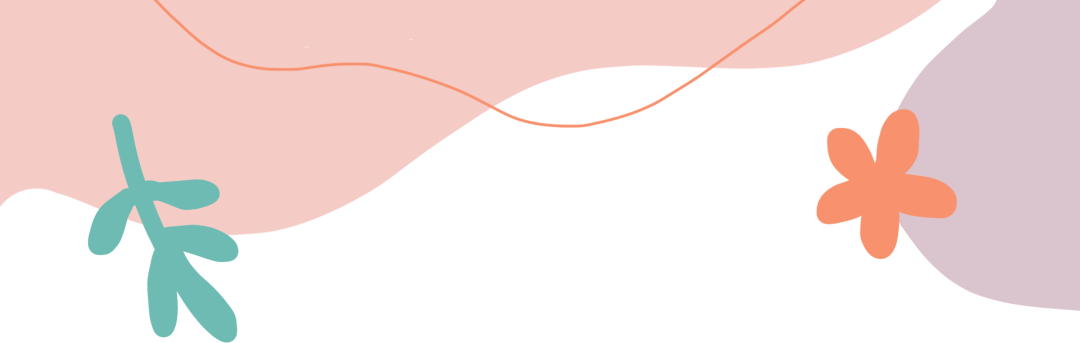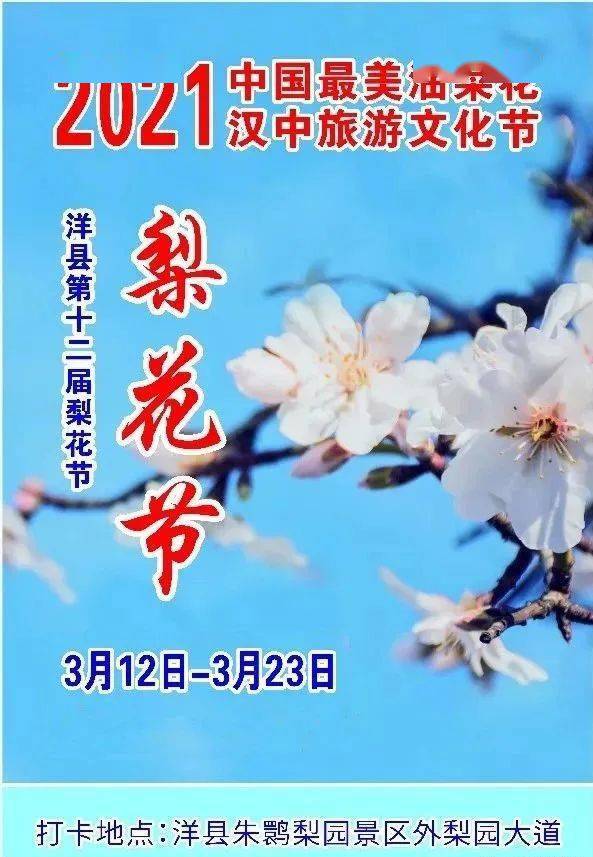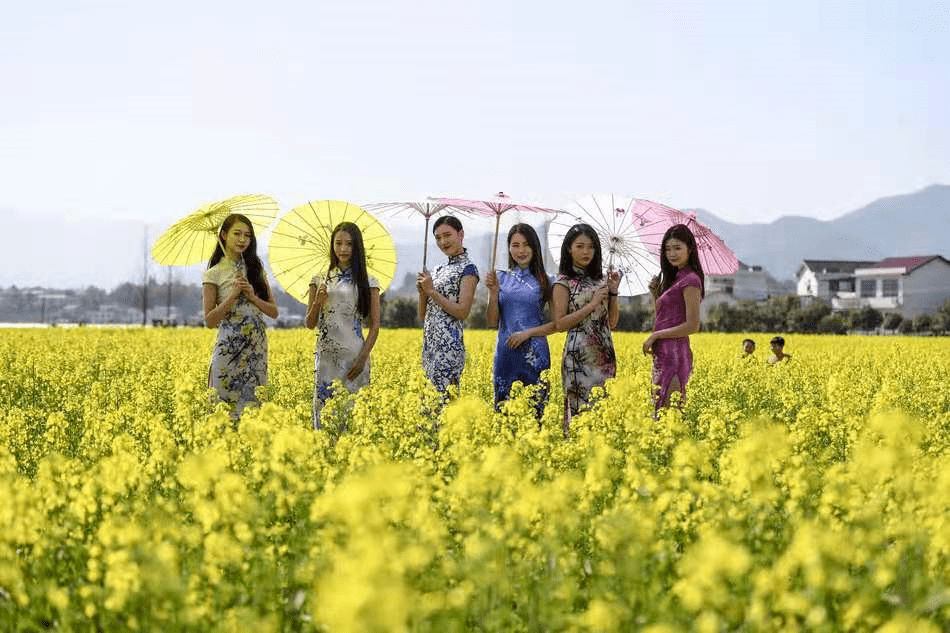俞启葆(1910~1975)字遂初。江苏昆山人。1922年离家去上海,入中华职业学校商科,1925年毕业后,在上海三友实业社当职员;1929年考入南通农学院附设高中,1930年又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农学院。在中大农学院,他边学习边参加棉花育种的试验研究,曾发表《中棉新品种》《中棉遗传研究》和《棉作叶绿素数量之初步研究》三篇论文,后两篇还被英国的农业杂志刊登、转载。1934年毕业留校,被棉花专家冯肇传教授选为助手,继续从事棉花遗传育种的研究,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又有两篇论文被英国遗传学杂志刊登,在国内外颇有影响。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忍着与亲人失散的痛苦,毅然随中大西迁重庆。1938年,随着南京、济南、开封、武汉的沦陷,中国的集中产棉区除陕西关中外,均被日军占领。俞心系抗日军民的衣被急需,曾利用假期作了50天实地考察,写出了扩大四川棉产区域的报告,递交国民政府参考。
1940年3月,经著名棉花专家冯泽芳举荐,俞调入国民政府农林部中央农业实验所。接着,以棉花督导的身份被派驻陕西农业改进所。到陕西后,他一头扎在泾阳农事试验场,与工人、技术人员一起,开展棉花的研究与推广工作。凭借自己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培育出棉花抗虫新品种鸡脚德字棉,选育出棉花高产品种泾斯棉,还成功地进行了亚洲棉与陆地棉的种间杂交。这一时期,他还抽出时间,先后考察了陇东、陕南、鄂北、豫西南棉区,提出了许多发展棉花生产、提高皮棉产量的建议,对促进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起了一定作用。他的这些福泽后世的科研成果,都是在十分艰苦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下取得的。那年月,重庆寄给他的薪俸虽然数目可观,但由于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待收到时,也就够每月买40来斤面粉填饱肚子,衣着花销再也无钱支付了。夏季棉田闷热难耐,他把唯一的长裤剪成短裤;秋冬天气寒冷,他在短裤外裹一件夹大衣,照旧在田间观察、在室内试验。有一年深秋,一个学校请他讲课,他就是穿着这套大衣裹短裤的特殊服装走上讲台的。尽管生活如此困难,他还把陆续获得的3000元奖金,接济了连饭也吃不饱的穷苦人家。
1945年初,俞作为留美实习生前往美国,当他来到指定的学校时,发现导师的水平不如自己。许多学者因为早就从他的论文中知道他的学识和才华,都无意收他为徒。在这种情况下,他首先考察了美国的所有棉区,接着在康乃尔大学选读了几门课程,后来又在克乃其研究所遗传学部住了三个月,写了几篇论文,满打满算在美国待了一年,便启程回国了。
留美期间,已传来抗日战争胜利的喜讯。俞急切地返回祖国,是想用自己的知识和在美国看到的现代文明为建设贫困落后的祖国效力。为此,他一踏入国门便奔走呼号,希望孙中山
平均地权的主张尽快实行,并说服母亲把自家的田地分给穷人;他马不停蹄地去鄂、湘、赣、苏、浙、冀、晋、豫各省棉区考察,力图发展棉花生产,解决国人的穿衣问题。然而,他的兴国富民梦想,很快就被国民党反动派的-、-和内战政策粉碎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和国统区一浪高过一浪的“反饥饿、反内战、反破孩”斗争,使他逐渐认清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真理。因此,南京解放前夕,当国民党-欲挟持中央农业实验所的高级知识分子去台湾时,他与同事相约:决不离开大陆,保护好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迎接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俞于1950年7月被任命为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技术研究室主任。赴任路上,他由潼关下火车,徒步前往西安,沿途查看田间庄稼生长,与农民研讨麦棉品种和耕作技术;思考着如何加强对西北13个农业试验场的技术指导,到任不久就草拟成《关于西北各省农业试验场的报告》。1952年,俞奉命筹建西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后任所长、研究员。195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农业部赴苏农业考察团,并任棉花组组长。1958年,西北农业科学研究所改称中国农业科学院陕西分院,俞任副院长,主持科研工作。中国共产党重视科学实验的各项政策,使他备受鼓舞,像一架开足马力
的机器,不知疲倦地工作着。在他的组织指导下,不仅找到了恢复陕西关中老棉区生产和开发河西走廊与新疆内陆棉区的途径;而且组织区域性大协作,从育种和栽培等多方面入手,找到了小麦条锈病和棉花黄枯萎病的综合防治技术,为陕西、西北,乃至华北地区的农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苦学力行、严谨治学的精神和只讲奉献、不思回报的道德情操,影响、教育了陕西一代农业科技工作者。曾被选为中国农学会西安分会理事长、陕西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还受聘担任农业部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委农业组成员,是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长期奔波在农村,生活无定,加上过度劳累,俞的身体日渐衰弱,1975年初竟至进食不畅。夫人劝他去看病他不听,只好求助组织;组织拿他也没办法,他日程表上的工作,依然每月每日都安排得满满的。7月参加省农村工作会议,已经咽不下饭,下肢浮肿,被送进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诊断检查,结果是胃癌晚期。消息传出,省委书记霍士廉等前往探望,指示医院全力医治,但为时已经太晚。俞丝毫没有悲伤。他压根没有多想自己的病痛,而是考虑如何抓紧这属于他自己已经不多的时间,处理他住院前还没有处理完的工作。他同各研究所的45位科研人员谈话,讲述了他对今后工作的意见;他给十几位在各地蹲点的科研人员写信,对他们正在进行的课题提出建议,鼓励他们勇于创新,早出成果;他还写信给上海复旦大学的王鸣岐教授,恳请王帮助陕西农科院植病专家刘汉
文搞好红矮病的研究。病危时刻,他想到他对中国的棉花生产还有许多话要说,便召来长期跟随他进行棉花研究的郑剑芸和温茂萱,口述论文,要她俩记录整理。当这篇题为《论中国棉种改革--兼论今后我国棉花选种》的论文初稿完成时,他已经不能下床了。工作上的事全部安排完了,俞才想到自己的家事,那是1975年9月12日清晨,他以微弱的声音向夫人和儿子、儿媳说:“我过世后,不要向组织提什么要求。”当天晚上便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