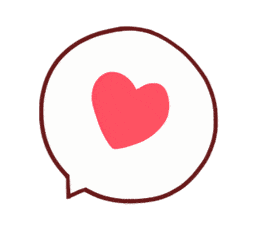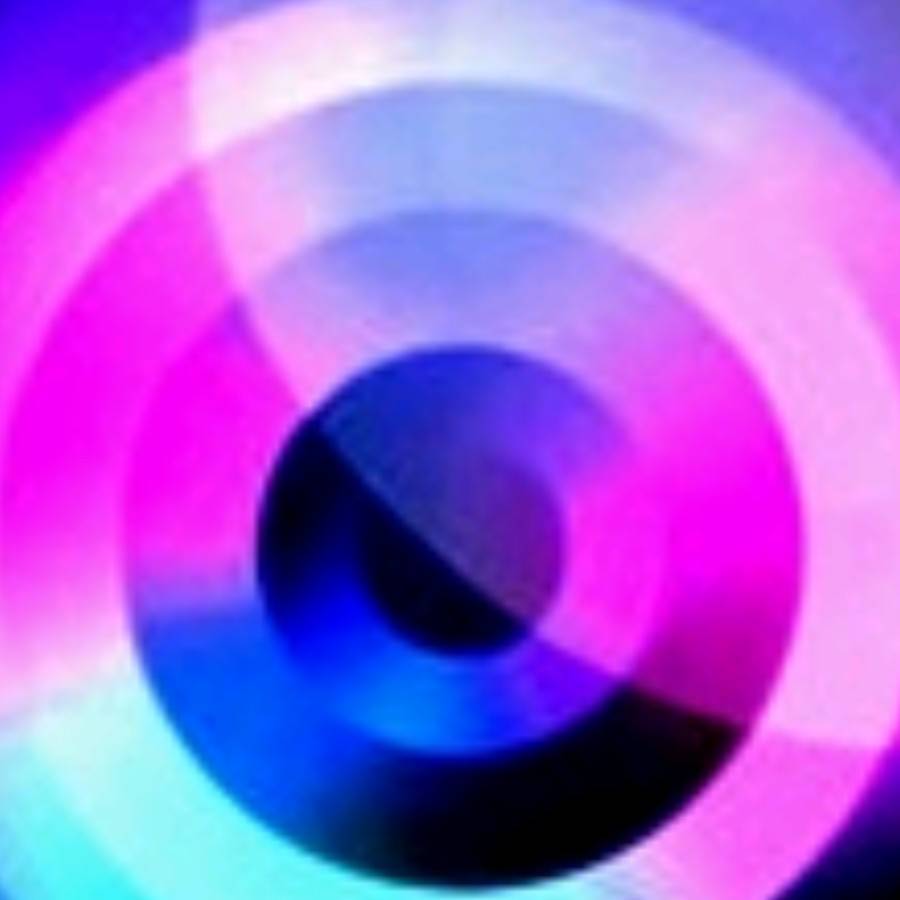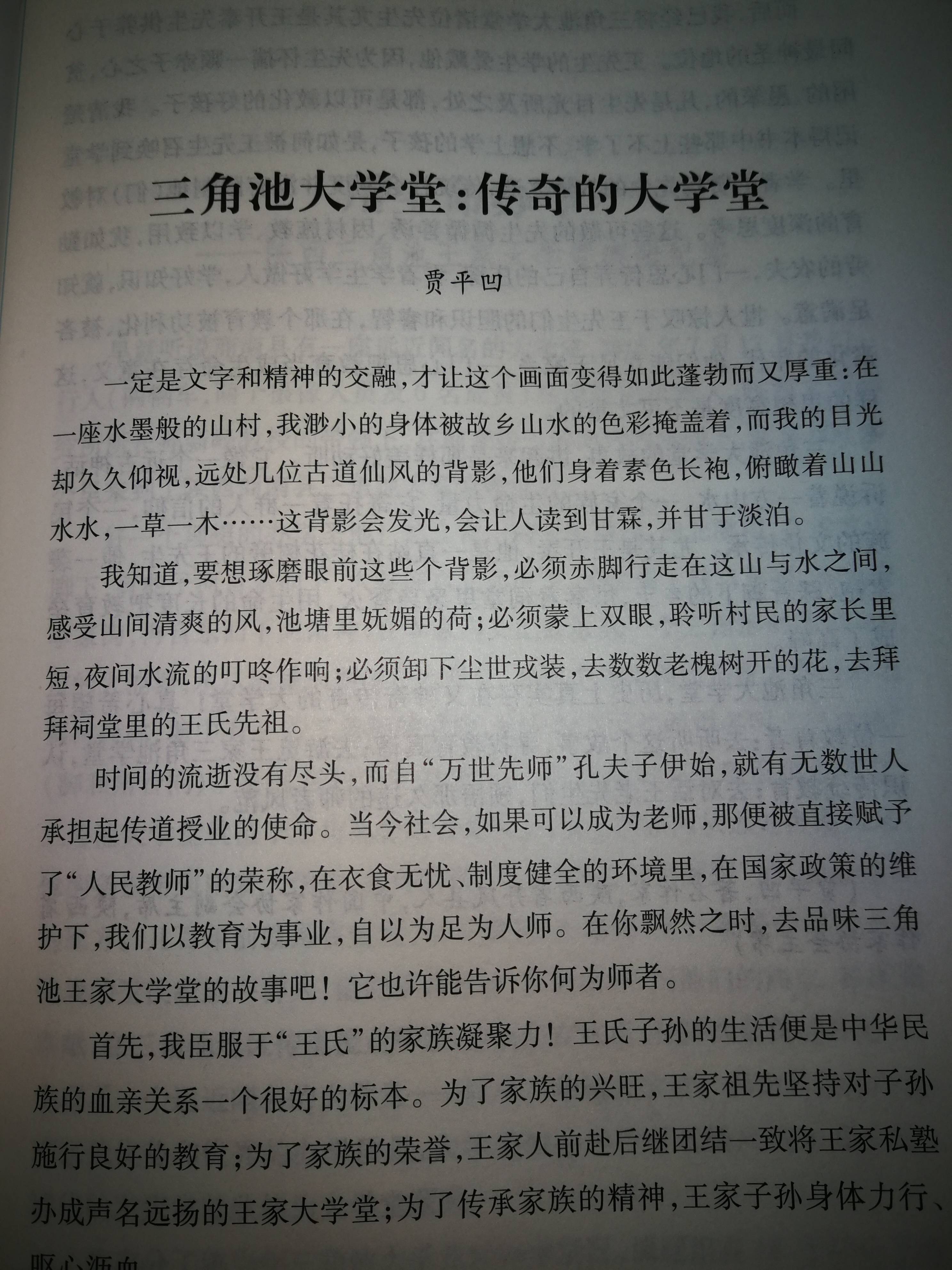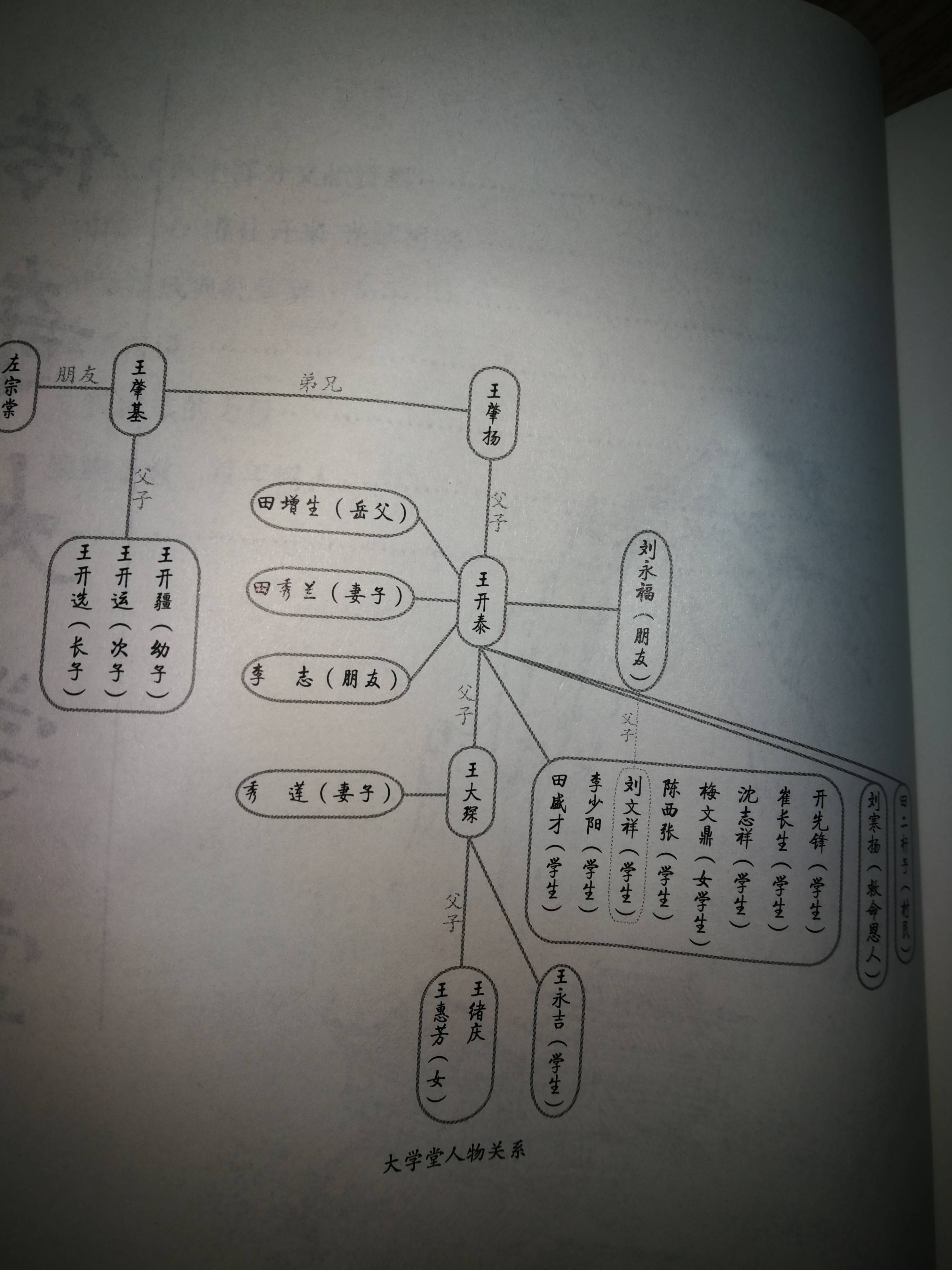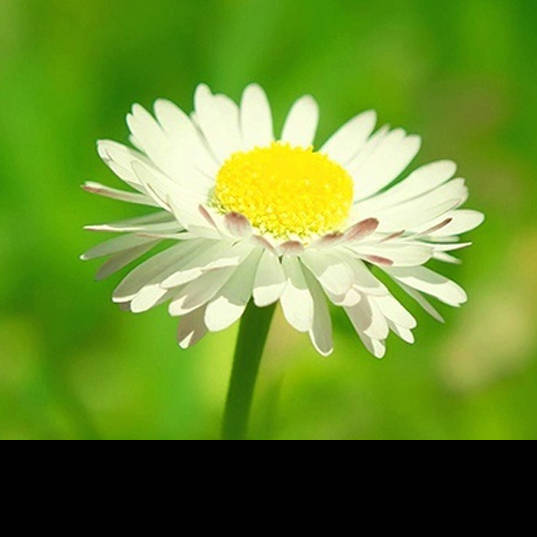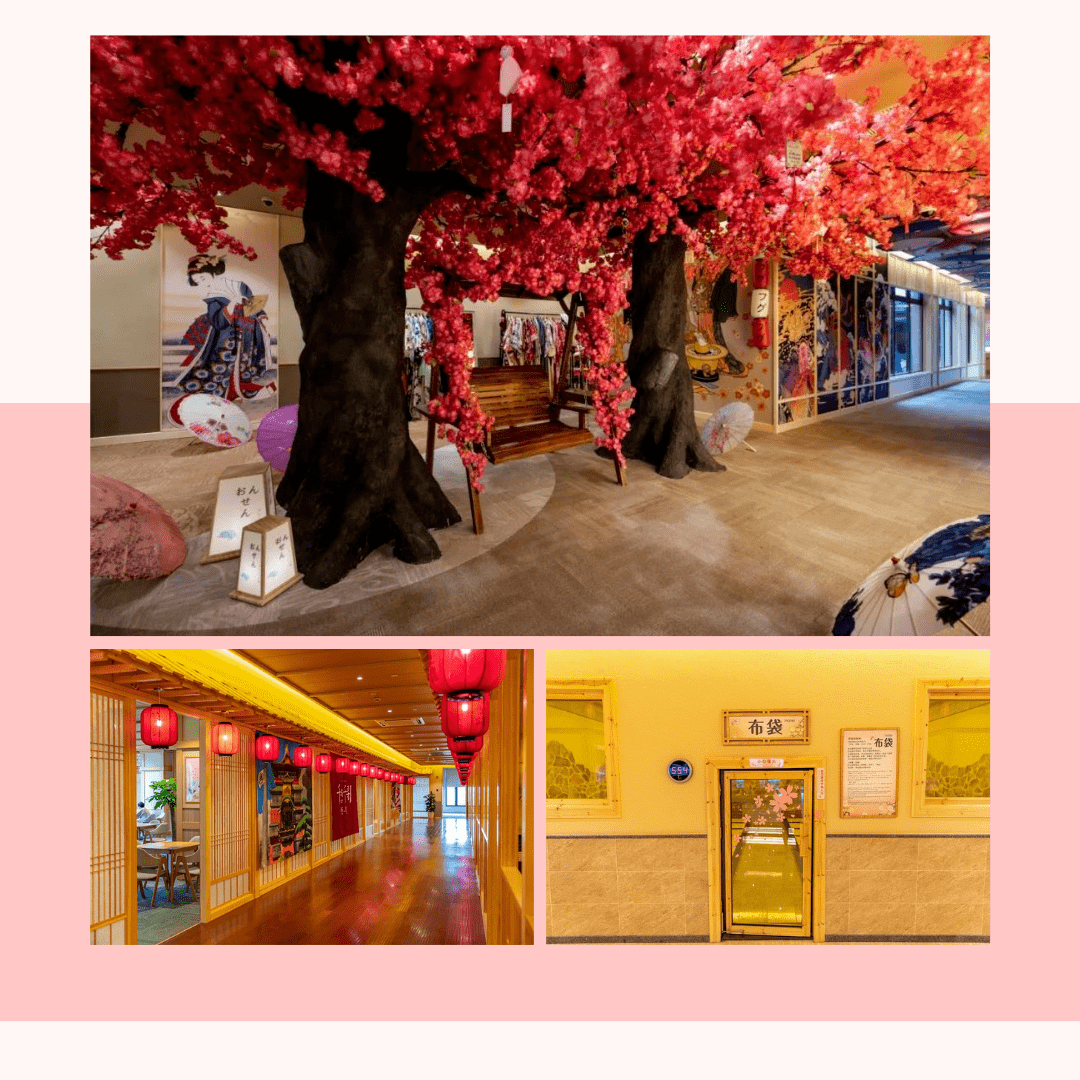李雨农,男性,四川省乐山市人,出生于1920年3月27日,1946年6月毕业于成都华西协合大学(七年制)医科。当时正处抗战时期,学校由三个大学组成,包括北京协和医学院、山东济鲁大学和成都华西协合大学。由于1945级学生提前一年(即1944年6月)全部应征入伍,参加远征军和军事机构,1946级学生也于1944年提前进入实习,直到1946年6月才正式毕业。所以我们1946级作了两年实习医生,受到更好的培训。毕业后,留校。任华
西大学医院外科住院医师。1947年6月受聘于重庆高滩岩中央医院,任该院外科住院医师。中央医院是在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极重要的医院,技术力量很强,人员多。
1948年春季,中央医院陈志潜院长在他的家中秘密召开了一次会议,选了一些中央医院的医生,准备筹建重庆医学院,所选的医生将成为医学院的骨干。外科只选了黄自强(解放后调北京301医院)和我;内科有曾承富(也调301医院)。1948年底,我被中央医院外科派至重庆大学附属医院:沙磁医院,(现重庆市肿瘤医院)主持外科工作并帮助提高该院业务。当时该院有四个医生,即王鲁直(解放后调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任皮肤科主任,已去世)、胡大鹏(解放后任该院骨科主任,已去世)、田德进(后调任歌乐山结核病院外科主任)和黄希岳(任该院外科主任)。
1949年10月,重庆面临解放,中央医院决定将我从沙磁医院调至中央医院城区
部,负责外科工作(解放后城区
部改为干部直属医院,后改为第三人民医院)。我下面有五个医生,即陈明琯(后任第三人民医院外科主任,已去世)、宁乾夫(后任第三人民医院泌尿科主任,已去世)、李福田(解放后调任四川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后任该院副院长)、陈熙(调外科医院任骨科副主任)、黄文(解放后任高滩岩三医大外科主任)。当时重庆是陪都,人口稠密,病人特多,每天忙于手术。
1950年大约秋季,中央医院调王安
定到城区部任外科主任。不久我被调至中央医院已接管的仁爱堂医院(该院为法国人创办),该院无外科,命我组建外科。并培训四个医生,即陈之寒(后调任北京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任外科主任)、里佐相(后调任重医附二院任五官科主任)、张思敏(任重庆中医研究所任五官科负责人,已去世)、姜医师(被调入西藏)。短短半年,从无到有,将外科迅速发展到90张床位,我被任命为外科副主任。西南卫生部为了解决病人多床位有限的矛盾,更重要的是发现中医的一些专科之所以存在有其必然的原因,经研究决定,要我继承、整理、发扬和提高中医的某些专科。首先给了我三个题目,即“中医枯痔疗法”治疗痔疮,“中医挂线疗法”治疗肛屡,“中医的骨折疗法”治疗骨折。西南卫生部鲁之俊副部长多次来院督促、检查。他亲切的夸奖了我说:“你的手术很好,但你这一生不可能亲手为十万病人手术,如果你在流行的中医疗法中进行研究,一旦成功,则亿万人民受福,你好学,会成功的。”接受任务后我从90张床中分出了20张床收治肛肠病,15张床收治骨折。一年多的临床工作,结合动物实验,改进了操作法,避免了毒效反应。
1952年,重庆市组成“重庆痔瘘小组”由陈之寒、周济
民、蒋厚甫和我组成,任命我为组长于9月去北京卫生部汇报研究工作,受到了卫生部的支持和肯定,并给予重奖。当时,卫生部命我小组在北京秦老胡同中直六院开展临床工作,并举办学习班,由我主讲,大约每三个月一次。到1953年共举办了四期,为全国培训了大批肛肠专业骨干。同时我还协助提高了六院外科的诊疗水平,所以中直六院想留我于该院工作。
1953年我曾在北京中华医学会作了两次学术报告,引起了医务界的高度重视,北京的报纸、电台,人民画报都曾以大量篇幅向国内外报道,有力的促进了中西医结合的发展。在北京期间,我常去鲁之俊部长家。有一次在部长家遇到重庆市卫生局何正清局长。吃饭时鲁部长说:“调他夫妇到北京中医研究院,唐德贤(我的爱人)主持妇产科,他主持肛肠科和外科。”何局长马上说:“不行,不能一次调我两个得力干部,唐德贤只能在五年之后才能调北京。”我着急了就说:“不行,她不能与我同时调北京,我也决不留在北京。”鲁部长很不高兴的批评何局长说:“他夫妇调北京是卫生部党委的决定,你能反对?”我得罪了何局长。同年秋季我回到重庆接家去北京,但我回渝后由于怕影响我的外科工作,借口不适宜北京的气候,不愿去北京,(只留下陈之寒、周济
民、蒋厚甫于北京广安门中医研究院)遗憾的为工作带来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