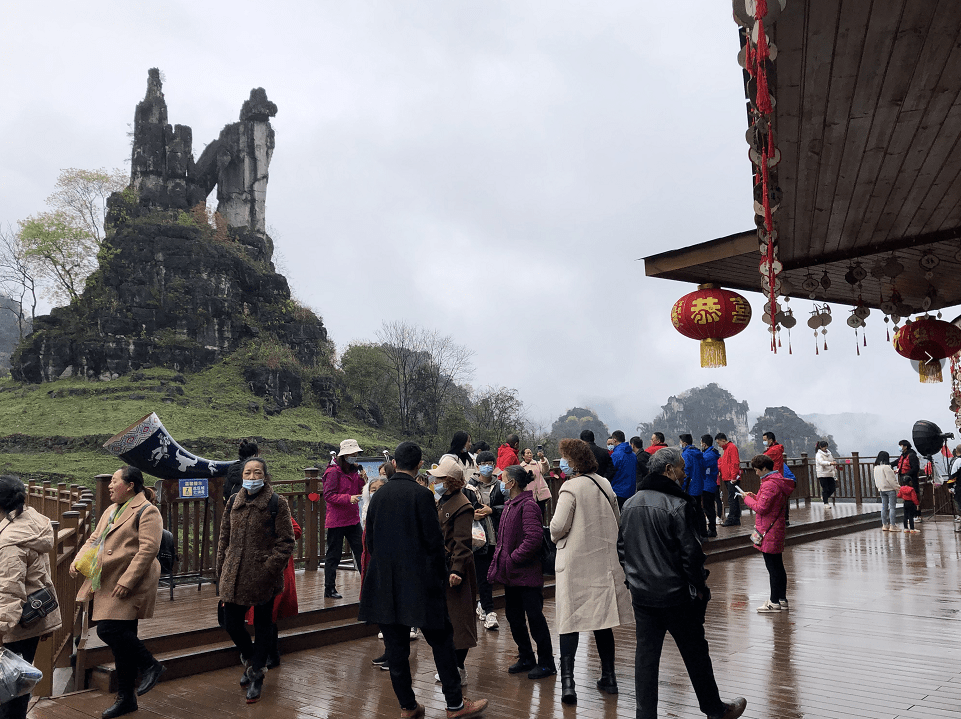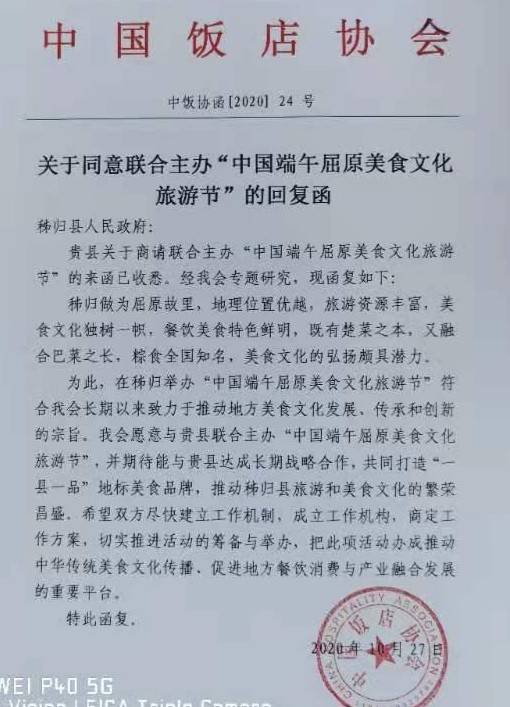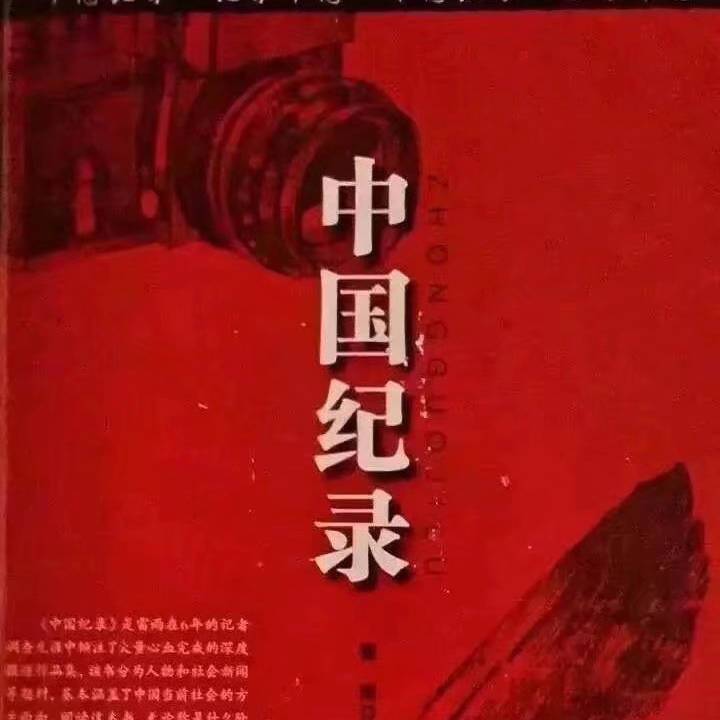鲜伯良(1903~1990年),又名骏,西充县太平镇人,重庆市第一面粉厂厂长,著名爱国实业家。西充县育英中学(前身西充县私立育英中学)创办人。
1920年,鲜伯良带着10多元路费,离开家乡,到重庆谋生,受聘于川康督办公署,管理财务,挣到了一笔钱。1925年,天津人单松年以4万元独资在重庆创办新丰面粉厂。1927年改为合伙经营,资本额增至10万元。鲜伯良投入股本3000元,担任了常务监察,后又担任协理。1934年新丰亏折过甚,无力继续经营。鲜伯良以9万元承顶新丰业务,改组成立了复兴面粉厂。
复兴厂成立后即正式申请注册为公司组织。所集资金除偿还必须付出的部分债务外,所余不过3万元左右,仅能维持2个月的产销费用。公司董事长鲜英,曾任川军十师师长,后又是刘湘部队的参赞;监察何化衡,系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其它如刘湘部队的军医处长贾文琴、财务科长朱大维、范绍增师部的经理处长李汝衡等,均分任董事和监察。在军阀割据,刘湘称霸的年代,有了这些军政要员参与,为复兴厂的经营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复兴厂改进技术设备,发展生产,同时精简机构,紧缩开支。对原有职工实行“汰弱留强”。鲜伯良认为,面粉销路是否能打开,关键在于能否降低成本,实行薄利多销。他发现在生产过程中无法将麦粒一次磨净,需经过几次回麸操作,不仅多耗工,而且影响出粉率和品质的提高。为了降低成本,必须解决操作技术问题。鲜伯良派员赴汉口参观福新面粉厂,请技师来厂协助改进技术设备,解决了不能一次将麦粒磨净的问题,日产量也由原来的300包提高到1000包。在产品销售方面,为了同先农、岁丰二厂竞销,复兴厂在市中区专门建立了特约承销店20家,签订合同,规定货源由复兴厂保证,不得承销它厂面粉。又利用水轮运输之便,在长寿、涪陵、万县等地设庄推销。市内外推销机构的建成,使复兴厂销量占重庆机制面粉市场的1/2以上。不久又因刘湘在绥定方向与红军作战,万县成为其军队转运粮秣的据点,面粉销量骤然猛增数倍,营业情况日益好转。因此,复兴厂成立后,第一年度决算就盈利。而先农厂由于历年亏折,虽经几度增资亦不能扭转劣势,拖至1935年,濒于断炊境地。1938年,先农终于无力继续经营,鲜伯良以4万元接顶过来,改为复兴第二厂。原厂命名为复兴第一厂。为了综合利用2厂储备的磨辊等主要器械,又添购了磨粉机三部,于1940年安装竣工投入生产。第二厂的日产量遂由300包提高到1200包。1943年南充面粉厂建成,安装磨粉机四部,日产面粉600包。于是一厂、二厂、南充厂日产量共为2800包。这是复兴厂发展最高峰
。
复兴争夺土制面粉市场是在与同业竞争中同时展开的。复兴厂发现土制面粉仍占全市销量的3/4,于是决定从批发和零售两方面进攻。零售,采取在邹容路口复兴公司所在地出售用特等面粉制成的白糖“蒸馍”的办法。由于地处交通要道,兼以免费供应茶水,确是顾客盈门,大有应接不暇之势。用次等面粉制成切面,在沿江码头劳动群众聚集处出售“旺实”面条。制成各种等级的干面,委托各糖果店代销等多种方法,所有零售均一律按批发计算。这样,从零售环节推销出去的面粉约占复兴和先农两厂总产量的1/5。市区80多户切面店,每月需用面粉20万公斤以上,但他们将机制面粉做的面条仅供特殊顾客之用,故数量少利润高,其余大部分面条都是以土粉为原料。为了消除这种人为的障碍,复兴厂特邀切面厂老板到复兴参观,表示已新装了机器,扩大了生产,一定要夺土制面粉市场而代之。同时大量散发广告传单,写上“怪!怪!怪!洋灰面当土灰面卖”的稀奇古怪的宣传话语,企图使他们改用复兴厂面粉作原料。为了扩大销售范围,特地做了大幅广告,鼓吹面粉所含营养远优于大米,外国人以面粉为主食,而我国北方人也是以吃面粉为主,故体格强壮。又鉴于重庆中医总是见到病人就说:“面食烧心,要忌吃面食。”鲜伯良感到这也是对推销面粉的阻力,就特备丰盛筵席宴请医师,大讲面粉的营养价值和有益于健康之类,希望摒弃见病即“忌面食”之说。这些都起到了一定作用。
在积极打开销路的同时,对于原料的收购更是不遗余力。在合川设庄收购小麦,以便了解货源和掌握行情,在重庆开设义厚生粮食商行,保证了原料的供应。小麦收购点进一步扩大到产区渠县、南充、射洪和宜宾等地。复兴厂业务蒸蒸日上,1938年纯利即达20余万元。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对面粉市场的价格,复兴厂已呈操纵之势,垄断了重庆面粉市场。
1940年以后,复兴厂经历由盛而衰的过程,同时也是进一步与军阀官僚勾结和斗争的年代。复兴厂依靠官僚和地方势力,基本上垄断了全川小麦,使得同业不但不可能在产区购进原料,就是在重庆高价收购亦难得手。为使产供销各个环节相互配合,对包装所需用的布袋,亦做到自产自用。在合川投资自行开设“七七”纺织厂,招雇200余名职工,专门生产布袋。产品既已畅销,原料又形成垄断,包装布袋也做到自给,因而复兴厂获利甚厚。
1941年,复兴部分股东集资法币100万元,开设万源企业公司,鲜伯良任董事长。为了扩大经营活动,筹资200万元又开设复华银行。复华银行成立后,更加壮大了复兴在面粉业和粮食市场的声威。复兴资金又助成了复华在金融市场上的活跃,因而人称鲜伯良为“灰面大王”。
抗战期中,复兴厂虽然一度出现过繁荣景象,但是遭受国民党政府的所谓限价和加工管制的摧残,到抗战胜利,原来比较充裕的原料存底已消蚀一空,流动资金亦亏赔殆尽。鲜伯良十分感慨地说:“在人吃人的社会,我虽然吃过‘小鱼’,但终于逃不脱失败的命运,官僚、军阀又把我吃掉了。把希望寄托在同官僚军阀和封建势力的勾结上面,既靠不住又是极端危险的。”
建国后,复兴厂在党的正确领导下,通过贷款和加工订货的扶持,还有全厂职工劳动热情的不断提高,很快就恢复和发展了生产。新建了1200平方米的车间和320平方米的仓房,从嘉陵江边到厂房建成起卸原料的电动缆车,从车间到厂房装设了梭槽运输道,还添置了磨粉机两部和平筛四部,学习推广了苏联的前路出粉法与中路刷清法等先进经验,从而节省了劳动力,生产成本显著下降,产量大大提高。单是复兴第一厂的日产量,就由原来的1000包提高到7000包,副产品也制成了大批工业用品的饴糖和食用酱油,每年给国家积累资金达10万元以上。鲜伯良受到党和人民的关怀,他当选重庆市第一至八届政协委员。
1990年5月,鲜伯良在渝逝世。